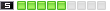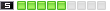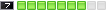雕塑《地狱之门》
为了《地狱之门》,罗丹用了一年的时间来阅读但丁的《神曲》,沉浸在但丁用文字塑造的虚幻世界里,用100多幅把书中描写的八层地狱画了出来,他运用中国水墨勾勒轮廓,用褐色水彩颜料衬出阴影,以体现出立体效果;有些画还只是直接演绎但丁的原意,如弗兰切斯加、乌哥利诺、地狱中形形色色的罪人,以及代表但丁本人的思想者。有的已不是简单的解释性的插图,而是评论性的阐述了。罗丹很快就对这个题材展开,引进了一系列新的形象。从这些新形象,不难看到诗人波德莱尔对他的影响。罗丹想要创造整个世界,把人类的种种感情都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除此之外,罗丹的足迹遍布全法国的土地,从都兰到艾瓦恩,从布列塔尼到勃艮第。他随身携带的速写本上画满了各式教堂的讲台、柱壁和整体模型,记了大量笔记,整整花了20年时间进行构思。而他越深入就越觉得这项工程浩大无边。政府曾多次派人来催促罗丹,并一再给他宽限时间,但他总是希望《地狱之门》上的人物多一些,再多一些。他为此画了无数草图,塑了一座又一座模型,但他总是不满意,一次又一次推翻原来的计划。其间,装饰美术馆已改设在卢浮宫的一翼,不再另建,大门的设计也不再需要,但《地狱之门》已成为罗丹雕塑的灵感的源泉,他无法从这个浩大的工程中抽身而出。
但丁的《神曲》以中古时期所特有的奇幻文学形式,写出了现实社会的种种景象,而其中的《地狱篇》实际上就是人间苦难的象征。现实生活中有贪欲、虚伪、嫉妒等许许多多不可宽恕的罪恶,人类必须为这些罪恶付出代价。“地狱”,就是人类自身的罪恶所带来的惩罚、痛苦、挣扎和绝望。以《神曲•地狱篇》为蓝本,反映了作为艺术家的罗丹对现实社会及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另一方面,也是罗丹强烈的宗教感的又一次具体体现。
《地狱之门》的规模确定以后,罗丹先用木料搭成一个大骨架,然后以黏土和石膏塑出种种高浮雕、浅浮雕和圆雕的群体及个体形象。
他始终处于《地狱之门》的创作狂热之中,这种热情他无法抑制也不能抑制,有时突然迸发灵感,即兴创作在一些雕塑中加进一个小形象,有时又会远观沉思,在深深思虑后又把它拿掉,甚至把它肢解开来,在断臂断腿上发挥新的想象。因此这件巨作永远没有完成之日。
最后我们看到的《地狱之门》,并没有全部呈现出他想放进去的雕像,这些雕像代表灵感的轨迹,是他“雕塑生涯的日记”。他当初想放进去的雕像太多了,两百多个形象置于整件作品中,无所谓对不对称,环环相套,组成一个纠缠盘结的庞然大物,罗丹决定砍掉许多人物。
《地狱之门》原定于1884年完成,但罗丹却一再拖延,历时37年,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完成。1900年展出的石膏像模型中,几乎已经完全删除了所有的圆雕像。罗丹去世后,《地狱之门》是由巴黎罗丹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最后定型的。1926年,应美国费城罗丹博物馆之请,这件巨作浇注成青铜雕像陈列在该馆。
希腊的诸神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对西方人审美判断力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希腊的诸神文明,是一种“人生的幸福、安宁、优美、平衡和理性”的文明;而基督教文明是以肉体受难和牺牲来换取精神崇高,是一种人格升华的文明。而罗丹倾心于基督教文明的深刻内省精神,倾心于悲剧所显示出来的力量。在他的心里,始终留有一块宗教的圣地。从最初的《埃玛尔神父》像,到青年时期的《施洗者约翰》, 到中年时期的《加莱义民》, 无不体现着雕塑家悲悯而庄重崇高的宗教情感。
《地狱之门》为了表现那些运动中的生命,雕塑了186个分别为情欲、恐惧、理想而不断争斗、折磨自己的形象。这当中,有雄健的躯体,也有柔美的裸身,其中的主要形象后来成为独立的作品。作品的中心主题是通过“地狱篇”中“从我这里走进苦恼之城,从我这里走进罪恶之渊,你们走进来的,把一切的希望抛在后面”的含义,用多结构形式和象征性构图及真实人物走型,综合表达罗丹的哲学观点,把近代文明罪恶都集中表现在“大门”之上,贯穿着希望、幻灭、死亡和痛苦等种种感情。
罗丹忘记了雕塑的纪念碑功能。他所做的不是歌颂丰功伟绩的凯旋门,而是一座“地狱之门”,这门上没有英雄,只有一些破裂、扭曲的生命。这也是一座“人间之门”,人间固然有欢乐和酣醉,但也弥漫着忧郁和厌世、烦忧和悲痛、陨落和伤感的气氛。这些悲惨、离奇、扭作一团的形象,正是罗丹对现实社会及人类命运激烈而深切的关照,也是基督般的悲悯的关照。不单单罗丹的作品表现出对人类心灵悲苦的依恋,与他先后同时的文学家雨果、易卜生、音乐家贝多芬都是这类典型。画家、雕塑家中,北欧的蒙克长于描绘心灵的忧伤和痛苦的意象,那幅撕人心裂的《呼号》,被罗丹称为“失乐园的呼号”。
德国画家珂勒惠支,在黑与白中交织着极端痛苦的人生悲剧,人总是在死神的阴影下挣扎。法国画家米勒,以表现巴比松农民的命运为己任,他看到农民的善良与纯朴,却“从未见到过欢乐的一面”。比利时的雕塑家麦尼埃,倾心于塑造普通劳动者的悲壮之美,他说:“黑色国土粗野的和悲壮的美使我震惊。”罗丹和他们是如此的声息相通!这些被称为“世纪末现象”的悲剧气氛浓郁的作品,表现了艺术家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剧烈对抗中的“杞人忧天”式的敏感。他们需要有内心强力的支持,生活与自然中的苍凉能唤起这种悲壮的力量。


 21世纪中国前沿影视论坛 → 电影艺术区 → 传统艺术 → 罗丹的雕塑艺术
21世纪中国前沿影视论坛 → 电影艺术区 → 传统艺术 → 罗丹的雕塑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