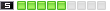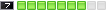学术文化电影《德里达》学术文化电影《德里达》——一个解构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视图化叙述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杨乃乔
2004年3月24日在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笔者有幸参加了由该校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关于传记电影《德里达》(Derrida)拍摄过程及其文化思想的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一次地道的国际性学术文化盛事,参加者全部都是来自于欧美、亚洲、非洲及大洋洲各高校及各科研机构的学者,其中包括这部电影的导演科比·迪克(Kirby Dick)和导演兼制片人艾米·瑟林·考夫曼(Amy Ziering Kofman),可谓语种、肤色混杂,在声色两个方面呈现出学术文化的多元性与全球性。
这次货真价实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是分为三个时段来展开的。首先,所有与会学者,带着一种严肃的学术期待眼光在一种视觉文化的轻松中,观赏了电影《德里达》,这部传记电影以写实的图像记录、叙述与阐释了当下誉满全球的法国哲学大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学术思想和日常生活,其实这也是一部学术文化电影;其次,与会学者们以极其高涨的学术热情聆听了科比·迪克和艾米·瑟林·考夫曼的精彩发言,发言涉及了他(她)们以电影的视觉图像叙述当今大师级学者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以及这部影片追录德里达学术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全部制作过程;再次,与会学者以多种语言与科比·迪克、艾米·瑟林·考夫曼进行了学术对话,对话涉及了用电影视图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表现的目的性与可能性,也讨论了在这部传记电影中的德里达于视觉图像中所呈现出的普通人所秉有的种种幽默及这位哲学大师每日生活中的常人一面。
在过去的40年来,德里达从一位最具争议的人物到当下走红于国际学术界的大师级学者,无论1992年剑桥大学在希望授予德里达以荣誉博士学位时,其在怎样的被嘲讽程度上遭到来自于其他各国的19位世界级学者的联系名抗议,但至少有一点是无法不让国际学界众多学者给予认同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颠覆西方文化史上漫长的形而上学传统时,他以极其深奥的思想与晦涩的语言完成了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从古希腊巴门尼德以来到当下的西方语音中心主义文化在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被“解理”的瞬间,全部坍塌。以个人的哲学思考来颠覆在印欧语境下建构了几千年的西方文化传统及其话语权力、价值观与美学观等,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撼人心魄。但关键问题是,在当下国际学术界,又有多少学者真正地理解了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思想?因此漫延西方文化传统几千年的语音中心主义文化又曾几度在德里达思想的“被理解”中全部瞬间坍塌?的确,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本在其思想的深奥与语言的晦涩上充满了拒绝理解的写作风格。上述19位世界级学者在他们的公开信中曾这样评价德里达:“他的作品采用了一种拒绝理解的写作风格。许多人愿意从善良的角度来怀疑德里达先生,坚持认为这样难以阐释的、如此深奥的语言一定隐藏着深奥、玄妙的思想。然而,只要作些努力(至少对于我们)即可清楚地识破:德里达先生任何表述清楚的断言,要么是虚假的,要么就是微不足道的。”(1)
以善良的批评断言德里达在哲人的睿智中所展开的解构主义思想是呈现于虚假中的微不足道,这似乎是另外一种偏激的观点,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及其思想的深度性、语言的晦涩性及文本的拒绝理解性的确是让任何曾经或企图接近德里达的学者给予充分的置疑。
不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德里达的理论的确是被拒绝理解的解构文本。当学术界从语言走向对德里达的解构文本在获取理解的意义充满了困惑时,科比·迪克和艾米·瑟林·考夫曼这两位电影人却另辟溪径,从电影图像的视角切向德里达,把德里达及其艰涩的解构主义理论带入电影图像的鲜活空间中给予记录、叙述、理解及历史化。其实,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设问两个基本问题:第一,这两位电影人为什么要用电影的图像方形式表现德里达?第二,用电影这种图像形式来叙述德里达及其艰深而抽象的哲学思想是否可能?
制作《德里达》这部学术文化电影的原创理念最早来自于女导演兼制片人艾米·瑟林·考夫曼。16岁的时候,考夫曼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家书店发现了德里达的著作,考夫曼是一位对哲学与艺术充满了本能感觉的天才女性:“德里达的著作是这样直接地告诉我——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像他这样的东西。德里达著作在一种最根本的方法上使文学与思想如此的鲜活而生动。”(2)正是由于源自于德里达理论的诱惑,没有多久,考夫曼就进入了耶鲁大学,并且一开始就师从于德里达,因为那时德里达正在耶鲁大学获取一个年度的教职。10年之后,即1994年,在洛杉矶考夫曼听完了德里达开设的一个讲座之后,决定为这位以个人的思考力量及其深度单独改变许多人看待历史、语言、艺术及我们自己的方法的哲人拍摄一部记录片,强烈的兴趣及理论的诱惑推动着她走上前去问德里达是否愿意拍摄一部关于他自己的记录片电影,但是,德里达一开始就断言拒绝了考夫曼。
其实,在考夫曼向德里达提出这个设想之前,其他学者也曾经试探地询问过德里达能否给他拍摄一部电影记录片,但是均遭到了德里达的拒绝。有趣的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一直因为思考的深奥及语言的晦涩而拒绝他者的理解,因此似乎德里达拒绝以电影视图的方式对他本人的理解与叙述,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这里有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从文字达向对德里达的理解本来就已经够晦涩而艰深的了,那么启用电影的视图化方式能够理解、叙述德里达及其玄而又玄的解构主义理论吗?因为德里达所研究的领域过于专业化,是很难借用电影的表现(cinematic representation)以视图来使其出场的。
然而,考夫曼并没有因此放弃为德里达拍摄一部记录片的设想,她近乎疯狂地给德里达打电话及发传真,以一种对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近乎痴迷不悟的关爱来陈述她的设想。执著的终结是允诺的收获,考夫曼终于收到了由德里达亲笔书写的明信片,但是,对于企图用视图来解释德里达的考夫曼来说,这张明信片简直是一个高深莫测的谜,因为德里达的亲笔书写是出了名的潦草,潦草到简直让人完全无法识别、无法理解。直到后来,考夫曼回想起来仍然禁不住地大声笑着说:“我最好从图像上假设他已经同意了。” (3)
无论如何,把德里达及其晦涩的解构理论视图化为电影记录片,这个解释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迪克与考夫曼两位电影人制作这部学术文化记录片《德里达》,这是他们应顺后工业文明高科技发展之文化节奏的必然。受后现代高科技视图语言的影响,用视觉图像的方式来记录、叙述与理解历史,用视图使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在一种鲜活的叙述空间中出场,这是学术界以高科技手段对所要研究的文字历史进行转换的尝试,这也是后现代高科技工业文明介入学术界之后对历史叙述方式的前卫性试验。的确,正如考夫曼在研讨会上接受众多学者的提问时所给出的启示:如果我们现在拥有苏格拉底对话的视图电影,如果我们拥有一部以视图记录笛卡尔、沙士比亚、康德、黑格尔及尼采他们的学术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电影,我们现在对他们的理解完全可能会不同于从书写的文本上对他们获取的理解,如果一部人类历史都能够用视图记录下来,在未来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借助于电影的流动性视图再度复现当时那种鲜活的历史场景,这样就可能使后来的研究者把对历史的理解降低到最小的误读限度上,同时,研究者也可以借助于视图在最大的理解程度上接近历史原初意义的本体。
其实,考夫曼作为一位年轻的女学者及电影文化人,当她在启动制作电影记录片《德里达》这样一种理念的瞬间,这已经不再简单地是在一种通常的艺术理念上怎样拍摄一部电影的问题了,她的行动已经介入了从施莱尔马赫到保罗·利科、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以来所关涉的阐释学理论及怎样使历史的原初意义再度出场的一个重要阐释学问题。需要提及的是,这部学术文化电影《德里达》的制作不再是一种抽象地从文字的角度空论阐释学理论的书斋学术行为,而是在后现代工业文明语境下一种凭借实践以电影视图记录、叙述与理解人物传记历史的阐释学方法论转换的行动。
在后来的几年中,于巴黎与美国,考夫曼始终以一位独立制片人的身份在用摄影机来追踪德里达,把德里达的这段学术历史视图化,然而,实际的困难使考夫曼考虑必须再找一位合作的导演,一如考夫曼自己所言:“我仅是一位学者,所以我的电影制作知识与技术是很有限的。” (4)
1997年,考夫曼出席了著名导演科比·迪克(Kirby Dick)《病者:鲍勃·弗拉纳根的生命与死亡,超级性受虐狂》(Sick: The Life and Death of Bob Flanagan, Super Masochist)电影的首映式。这部电影的首映式上,考夫曼被迪克这部电影的反庸常性艺术思想所震动了,《病者》是一部表现性受虐狂的文化记录片,但是迪克通过电影视图的表述拒绝把价值判断强加在性的偏执上,仅从这样一种艺术思维的视角来看,迪克不是一位落俗套(stereotype)的导演,他的导演意识是相当开放的,对于在《病者》这部电影中所表现的主题,他没有就角色进行高下主次的等级划分。考夫曼认为,迪克是在一种自觉的方法中打造出一个范本,打造一种德里达式的规则,即在任何一个相对立的系统中很难用一种特权的方面压倒另一方面,正如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在消解一个中心时,并不是主张再度建构另一个中心。迪克同样也被考夫曼所拍摄的胶片点燃了他的热情,迪克说:“看看考夫曼所拍摄下来的材料,我为她所抓拍的独特而切近的场景而感到震惊,同时也被德里达那种极富魅力的镜头形象所激动。我告诉她说:‘很好!你捕捉到了你的明星。’” (5)
实际上,虽然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之父及其著作在欧洲名噪一时,但是长期以来德里达总是回避在公共场合表现他个人的超凡魅力。考夫曼在研讨会上回忆道:“直到70年代后期,德里达不但总是拒绝拍电影,而且绝对地拒绝拍摄他的照片。即使那个时候他的解构理论其及著作已经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他长的是什么样。德里达过去和现在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个人崇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荒谬可笑的。然而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为公共事业的利益而从事公共活动。在那个时段,出版界在学术界不断地刊印德里达的一张照片,但是我认为出版界刊印的这张照片是米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的,他们错误地把这张福科的照片认为是‘德里达’。其实,德里达拥有一头让人难以置信的浓密的头发,从那时开始,德里达意识到他是无可逃避的,他开始接受了媒体:‘如果他们愿意在任何地方刊发我的照片,那最好刊发一张正确的照片!’” (6)
电影作为艺术门类中的贵族品类,其跌向大众传媒的受众层面在于电视频道的扩放与DVD光盘的廉价复制,在后工业文明高科技发展中崛起的大众传媒业对当下社会及文明的冲击给人们带来充满种种可能性但缺少幸福感的躁动。用考夫曼的话来讲:“这是德里达第一次同意摄制的记录片,也是第一部实际完成的记录片。” (7)由于德里达的著作及其语言书写规则有着相当的严肃性与哲学性,他特别担心把他的研究严肃而精确地转换为另外一种视图媒介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一个画家的绘画作品转换为文字一样,也正如爱因斯坦用抽象的数学公式谈完了相对论后,我们还是无法在意义上准确的理解他,于是我们可能会这样设问爱因斯坦,你能够不用那些公式再来解释相对论使我们明白它的意义吗?然而,人们面对德里达时也同样带着这种热切的期待。正是因为德里达表述其解构思想的媒介是语言,这意味着你通过大量的学习、阅读与准备就可以理解德里达,然而我们是否能够通过电影视图来叙述与理解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理论呢?德里达就曾经给迪克与考夫曼讲述过一个让他们在电影中用视图无法表现的趣事。
由于迪克的加盟,学术文化电影《德里达》制作的成功充满了可能性。对于迪克来说,他之所以加盟《德里达》,主要的吸引力之一恰恰在于实现这个计划似乎是没有可能性的。迪克说:“我曾经阅读了大量的法国理论,这些理论曾对我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特别是《病者》。如象《病者》一样,德里达绝不是一位可以简单直接表现的人物,还有他的著作也是如此,但这也是一次在德里达及我们制作人之间进行不断互动的检验。然而,由于德里达的著作是非视觉化的充满了思辨的抽象性,所以对于影片制作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正是这次挑战把我吸引到这个计划上来,并且我也知道这次的挑战迫使我一次再一次地回到关于德里达的材料上去,最后使我的拍摄找到了一种以电影视图来转换德里达思想的形式。” (8)
当这项摄制工作重新开始时,迪克与考夫曼进行了密切的配合,他们两人决定还是由考夫曼来做第一采访者,他们一起来编写由考夫曼向德里达所提出的诸种问题。在后来的两年多期间,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厄湾分校拍摄了德里达在那里两次不同的讲学,也安排了海外摄制组拍摄德里达在澳大利亚的访问及其对南非的第一次访问。
在2000年初摄制组返回巴黎后,再度拍摄德里达在那里的学术与日常生活,并请他本人谈一谈用电影这种视图形式对他的理论及其解构主义思想进行转换与阐释的反映。
在坎特伯雷大学举办的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者在与迪克、考夫曼进行对话时,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感觉到,其实,迪克与考夫曼以视图记录、叙述与理解德里达行动的本身就是一次解构行为,的确,他们是在操用摄影机来为后来的德里达研究者制作一部可以视听的图像历史,这种视听的图像历史在方法论上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文字历史所给出的一种破坏与重建,其实也就是在历史的叙述形式本体论上,以视图替换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在解构与重构之间的转换,即用视图历史解构文字历史,视图历史对文字历史的解构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构,这是一种在后现代工业文明景观下以视图传媒叙述历史的崭新观念。关于这一点,迪克与考夫曼在研讨会上表述的非常清楚。因此他们在行动的理论上是自觉的,他们也是解构主义者。有趣的是,德里达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时,张扬的是文字,他把文字认定为是嵌放在意义与声音之间,使意义延缓出场而产生差异的衍生物,德里达认为,受控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下的由拼音文字建构的西方形而上学文化传统,正因为与原初意义之间存在着理解的差异性,所以由文字使意义出场的形而上学历史是虚妄的历史文本。德里达把文字嵌放在意义与声音之间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也颠覆了由文字书写的历史,而迪克与考夫曼在追踪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时,又企图用视图叙述历史从而解构了文字历史。
所以,拍摄这部电影的迪克与考夫曼,他们也是地道的解构主义者,并且以图像解构了文字。德里达张扬文字,在于文字与历史的原初意义之间存在差异,而成立自己的解构主义理论,迪克与考夫曼干脆以图像直达对历史原初意义的记录、叙述与理解,企图边缘化了文字,这大概是德里达的悲剧。
迪克与考夫曼在拍摄这位以“解构”而满载名誉的哲学家德里达时,他们跟随德里达,以图像写实德里达第一次到南非的学术旅程。在南非德里达访问了曼德拉以前被囚禁18年的监狱,在开普顿著名的西开普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Cape)德里达给那里的学者开设了名题为“宽恕”(forgiveness)的讲座。电影摄制组还跟随着德里达从他巴黎的家来到纽约,在那里他讨论了传纪作者的角色,讨论了当一位学者在一位历史人物研究与生活之间的渊潭中力图架起一座桥梁时所面临的挑战。电影摄制组捕捉了德里达许多私人生活的瞬间及话题,如忠诚与婚姻、自恋与名声、还有关于性生活及爱的哲学思考的重要性。
据两位电影人介绍,2001年,迪克开始剪辑这部电影,他把焦点定位在这部电影的中心主题之一,即德里达本人所提出的:怎样把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与他们的生活整合在一起?完全消除两者的关系,即如海德格尔与德里达自己反复指出的那样。在编辑这些材料时,迪克的挑战使德里达的生活与思想给予很好的整合与互动,他没有简单地用一方来解释另一方。包括德里达在拒绝与回避问题时的有趣表现,还有反复地提醒那些在访谈的种种环境下的不自然的观众,这些都是迪克的基本观点。这些个人的有趣的侧面都是德里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他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踪迹所在。强调这些侧面的瞬间可以消除这样一种偏见:德里达不是为了艰深而固作艰深。这部电影作为视图媒介为我们提供了边缘于解构理论思想之外的关于德里达的常人信息,如小的时候,德里达因为胆小几乎每个晚上都哭着叫:“妈妈,我害怕”,因此妈妈让德里达睡在自己旁边的沙发上,其实后来德里达的父母亲从来没有读过他的著作。德里达曾因是犹太人而被开除学校,他曾经取过一个秘密的名字,即犹太人的先知“以利亚”,但是这个名字并没有登录在他的出生证上。他曾在15岁时撰写过他的第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是关于一本日记失窃后为了找回进行勒索的故事。他在参加高考时,第一次就失败了。他曾因为权威人士安排他挟带毒品而在布拉格被捕,结果在监狱里被关押了24个小时。德里达脸部的一面曾经麻痹了三个星期,眼睛一直无法闭上。他曾接到过一个电话,打电话者把他错认为海德格尔。他曾经拒绝过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邀请他在她所拍摄的电影中担任一个角色。在青少年时代,德里达曾梦想成为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德里达没有给他的儿子们实施割礼,这让他的父母非常地恼火。德里达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和神经官能症,并且过量地服用安眠药和安非他明。总之,从这部电影的视觉叙述,我们可以触摸到在晦涩的解构主义立场之外,还站立着一位作为普通人展显自己的德里达,这个德里达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迪克是选择从德里达的著作中进行观点摘录,然后围绕着这些摘录的观点来结构这部电影的:“我想要转换德里达书写中的声音与节奏,因为书写总是完全不同于一位作者言说的方法。由于在许多情况下,德里达的书写风格与其内容是一样的激进且鼓舞人心,所以对于他来说,这是特别的真实。如果不能捕获那种声音的意义,一个人就不能够真正地理解德里达寄于书写中的雄心。” (9)由于这部电影和德里达书写中最为精彩的主题之一,就是一位哲学家个人的生活是不可必免地联系到他自己的书写,德里达是作为书写者或言说者通过书写在主题中来表现他的立场的,迪克就是从反映德里达立场的主题中来选择这些摘要的;比如,关于德里达在为一个学术讲座做临时准备时检查自己知识盲点的摘要,关于在德里达与他临终前的妈妈说话时分析自己话题立场的摘要。
考夫曼在电影中采访德里达时曾这样问德里达:如果你在看一部关于海德格尔、康德或黑格尔的记录片,你希望能够了解他们的什么方面?德里达说:希望了解他们的性生活,如果你需要我尽快地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要听他们谈一谈他们的性生活,正因为他们不讨论这些事情,我就是想听一听他们拒绝讨论的事情。为什么这些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表现自己时不关涉他们的性生活?为什么他们从自己的著作中抹去他们自己的私人生活?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没有比爱更为重要的了。(10)从这部电影的视听上,当我们捕获到德里达在一种谨慎的幽默中把海德格尔、康德、黑格尔与关于他们性生活的设问调侃在一起时,我们可以体悟到这位思想大师在冰冷的哲学思考表象下所遮蔽的庸常人性一面。
在这次研讨全上考夫曼认为,“我最强的协调性就是我曾经跟随德里达学习,曾经给学生们讲授德里达。我不会受材料的束缚,可以对材料进行分析,在几种层面上来制作电影。我希望德里达艰深的思想不是推脱的借口,而是其要求的一个中心部分。这部电影绝对是不一种说教——而使你参预到德里达关于解构的全部著作中来。如果你看完这部电影后,还不能正确地理解什么是解构,尽管如此,你已经简便地与电影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互动从而开始把握解构了。” (11)考夫曼补充道:“另外一种诱惑即拥有一部关于这个人物的历史电影档案是我们的简单愿望。今天我们能够从电影上看到柏拉图或尼采及他们的生活时代,这不是非常有趣吗?在今后的几百年内,拥有一部关于德里达的电影档案,这是极为精彩而重要的。” (12)但实事求是地讲,当我们看完这部《德里达》的影片后,关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体系,我们还是无从准确地把握。关于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踪迹、差异、形而上学的等级序列等一系列术语及其内涵的被理解,似乎让我们无法、也不可能从图像上提取准确的意义。在这部电影的摄制过程中,自始至终,德里达绝不正面地谈论电影或传统的传记肖像问题。也就是说,操用电影等图像形式来记录、叙述与理解一位显赫的学术人物及其思想是否可能?并且是在一种怎样的理解程度上可能?还有待于我们质疑。我们的初步感觉是,《德里达》这部电影所记录、叙述与理解的全部理念,其所接纳的受众还只能是那些少数阅读过或研究德里达及其著作的专家与学者,当然也包括那些对德里达充满着崇拜感且对德里达的思想获有一知半解的大学生。需要提及的是,电影《德里达》被刻录为DVD光盘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及学者性个人家庭媒体上广为传播。这部电影在捕捉解构理论的基本氛围中打造了一个普通人形象的德里达,这是让人不容置疑的,因此源起于当下国际学术界对德里达的种种崇拜而加冕在他一头银发上的圣哲光环被解构了。
总之,他们用电影视图在重构常人德里达时,解构了圣哲德里达。
需要提及的是,关于《德里达》这部当代哲学巨星的电影制作可谓是明星打造,导演迪克在电影文化界是一位名声显赫的多次获奖者,他最近拍摄的三部影片曾经在太阳舞电影节(the Sundance Film Festival)的纪录片大奖赛上首次公演时获奖。1997年,他导演了在国际文化领域获得好评的电影《病人》,这部影片在1997的太阳舞电影节获得了特别评审团获,又在1997年的洛杉矶独立电影节(Los Angeles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获大奖。迪克的其他几部电影包括具有相当创新性的《连锁镜头》(Chain Camera),在太阳舞电影节首映时由于这部影片的戏剧性冲突,在评论界获得巨大的反响。他的第一部长片《私人的实践:一位性代理人故事》(Private Practices: The Story of A Sex Surrogate),在美国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大奖。迪克刚刚封镜了一部影片《终结》(The End),这是一部深入了解洛杉矶收容所五位晚期病人及他们家庭病史的纪录影片。迪克是一类崭新的电影系列制作人,其声望极高被称誉为“美国密秘”探索电影系列。
电影《德里达》标志着艾米·瑟林·考夫曼作为导演的首次登场。1980年考夫曼在耶鲁大学从德里达学习博士课程。她刚刚完成了一部受到批评界关注相当具有个性的纪录片《泰勒的竞选》(Taylor's Campaign),这部影片追踪了一个种族的那些无家可归者之一,叙述为了种族而竞选桑塔·莫妮卡市(Santa Monica City)参议会一个席位的故事。
电影音乐的制作者是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他也是一位世界级的作曲家,他曾为贝多鲁奇(Bertolucci)的电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所配写的音乐获奥斯卡奖,并且他曾与众多的世界级大导演进行合作。电影《德里达》的音乐充满了无调性、无主题的无结构感,音乐的调性解构色彩及无旋律的音响随意流动性烘托起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在电影的视听文化中四处弥漫,坂本龙一似乎让受众在音乐“声音”的流动与倾听中理解什么是解构。
总之,这部电影所表现德里达的那种满头银发的哲人风度,由奥斯卡音乐获奖者坂本龙一谱写的让人不知所措的迷人音乐,编导在表现德里达时所创造出来的丰富情节,真实的电影体验立刻可以激发受众进入视听阅读的欣喜与愉悦。电影人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德里达,一个不拘小节的“解构”典范——一个现在仍然回避电影拍摄的思想体系。这部电影不仅是德里达思想及日常生活的视觉击活,而且也为学术界以图像重写历史及历史人物开辟了新的领域。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可谓是高潮迭起,当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学者操用多种语言激情于解构理论的晦涩性与电影形式的视图化在跨学科整合中是否可能等诸种问题的讨论时,一位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法国学者操用带有法语色调的英语不无自信地从众声喧哗中凸显出来:德里达在法国已经是过时的人物。
2004-07-17写于坎特伯雷大学
《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10日与22日连载。
(1) 《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3页。
(2)(3)(4)(5)(6)(7)(8)(9)(10)(11)(12)引文来自于科比·迪克和艾米·瑟林·考夫曼在坎特伯雷大学主办的关于传记电影《德里达》拍摄过程及其文化思想学术研讨会上与诸位学者对话的记录及他们的发言等材料。


 21世纪中国前沿影视论坛 → 电影专业区 → 影片分析 → 学术文化电影《德里达》
21世纪中国前沿影视论坛 → 电影专业区 → 影片分析 → 学术文化电影《德里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