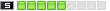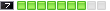百年西部片——西部片之“初” 百年西部 西部之“初”
“当传奇与现实相遇,留下传奇。”
--约翰·福特
有心人回过头来再看世界电影这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会很惊诧于美国西部片在世界影史上那颇有分量的江湖地位。这应该是电影最早开辟娱乐潮流的一座不朽丰碑,风格粗中有细,实践色彩浓郁,几乎是为后来所有的娱乐类型片提供了不等价的资源借鉴。如果说二十世纪初英国学院派真正创造了缔造电影二度革命的诸多新技术,譬如剪接、特写等新兴气象,但是真正纯熟地将这些新技术发扬光大、并能掀起追逐热潮的类型电影,还当属西部片的崛起,居功至伟。
1903年,一部《火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于美国诞生,让“西部”这个视觉概念的雏形与观众不期而遇。影迷们惊呆了,其刺激程度并不亚于当年法国人看到火车驶来就四散而逃的戏剧场面。被第一次实践的画面复合技术,令飞驰的火车与狂飙的奔马相得益彰,而模型道具的巧妙运用,更让人们感受到了以假乱真的电影魔力。虽然只是十分钟长短的小段子,但是故事的跌宕与紧凑,以及动作场面的惊世骇俗,却是让人击节三叹,不得不额首道上一声“妙哉!”。
抢劫钱财的土匪,用最为古老的追逐方式挑战着现代速度的权威,这就是骏马追赶火车的画面带给人们最直观的概念冲击。单枪匹马的所谓“英雄”开始奇迹般地跃身于火车顶部,像征服一条暴龙一样展现着自身的豪情与征服者的快感。这种快感是枪支所不能匹敌的,所以说那精彩刺激的火车枪战与徒手搏斗,已经全然成为了拼凑时间的陪衬。特技技术的初步运用成为这部电影赖以成功的法宝,它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观念,更让西部片这个概念如同古希腊传说中那征服暴龙的神职勇士一般,成为人们口中的谈资与心灵的震撼。
自此,好莱坞的电影工业里开始崛起了一干打着西部旗号的新贵,当然也不乏通过《火车大劫案》一片而一步登天的著名演员比利·安德森。当他开始自在地享用“野马”这个外号时,他已经作为一个时代的现象,开始衍化为了流行前沿的一种特性符号,这种符号更类似于五十年代初期比尔·哈雷将摇滚乐带上电影银幕,亦或是六七十年代纵横于流行前沿的摇滚之王“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他们引领着好莱坞这个大家庭从北方迁徙到了西部,在加利福尼亚州这块待垦的荒原扎下根来。当然,他们并不是像真正的牛仔一样跨着墨西哥骏马、嚼着哥伦比亚烟叶、哼着弗拉门戈小调、衔着苏格兰口琴、挎着考尔特象牙老枪而来的;他们是被火车这个现代交通的流行怪物载运来的。在通往旧金山的单轨铁路上,一群造梦者躲在木质车厢里,吃着考究的瑞士牛排、品味爱尔兰果子红酒、扛着来自自由法兰西的单极摄影器材憧憬理想,他们注定要扎根在西部创造一个惊世骇俗的人间奇迹,为自己的英雄之路谱写下最为伟大、最为靓丽的浓浓一笔。
一、
有许多论述中讲到,西部片的崛起与流行是美国人追逐自由生活理想,以及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一种叛逆式心理宣泄。从“大淘金”时代迁徙而来的梦想者,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消磨而扼杀自身的冒险天性。他们反而会尊奉那些习惯于“虎口拔牙”的惯匪为英雄,把对抗制度束缚的惯犯当作自己的偶像甚至是图腾。这样的例子是不需要刻意举证的,马克·吐温也时常慨叹道,美国人民的喝彩与白手帕宁愿留给那些扫荡了南北十几州郡;惹下无数人命官司;玩过无数美女;抢劫无数金银;被判无数罪状的大盗,也不会给予那些只会玩弄权术;一派道貌岸然;说话冠冕堂皇;糟蹋纳税人钱粮的职业政客。这句评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将美国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全然点破,毕竟这尚且是个新兴的国度,那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们千山万水地踏上这片土地无非都是在做着或大或小的发财梦,他们需要的是金钱与糜烂的生活,而决不是一个号称天堂、标榜自由的国家。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论断还是颇为浅薄而偏激的,偏颇得像一群贵族倒卧在象牙塔上讨论贫下中农们的审美意趣,以及喜怒哀乐。正如一向鄙视好莱坞电影造梦工程的法国主流电影评论,如《回声报》、《电影手册》在六十年代也开始正视西部片的渊源一样,人们是需要以一种对待艺术的心态与方式去重读这一段历史的。西部片不仅仅为电影家族带来了一种为娱乐而衍生的力量,更为世界电影成熟地实践电影技术提供了相对广阔的舞台与空间。以文化的角度而言,它的崛起并不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社会现象,更多的是对欧洲近代大众文艺的一种继承与演化,甚至是一种相对于生活状态而言的文化歧变。
近代的“西部传奇” 给世界电影创作实践带来的第一个革命,就是对欧洲主流文学与个人价值观的一种颠覆,平民对骑士生活的推崇,以及剑客行为捍卫自身尊严的社会潮流,就是一个根本无法被主流秩序所承认的一种“模仿式” 的个体报复行为。以大仲马为首的主流作者笔下的英雄,是体制内具有相对身份的士绅阶层,他们不具备大众平民的代表性,但是身上的品格却是让人赞叹。《三剑客》(Three Musketeers 1974)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当然会被纵横于市井的人所不屑,他们或许更需要一种驰骋于山林草莽之间的“侠盗罗宾汉”,需要这样的不法之徒对旧有制度形成一种革命化的威胁,当然他的个性最好是习惯于独来独往的独行侠,只能给王公权贵捅一些小漏子作为示警,而不会作为真正的势力重新定位已然根深蒂固的社会制度。这时候的人们是相对自私而简单的,他们拒绝不必要的社会动乱。
有了《大鼻子情圣》(Cyrano De Bergerac)以后,人们开始对士绅的骑士生活感到有点厌倦了,在世人眼中,他们是自卑的,懦弱的心理如同皇帝的新装一样,开始以不遮羞丑的方式向世人自欺欺人般地显摆。而《基督山伯爵》(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已经很不一样,不择手段的权谋与忤逆于传统的混世方式,已经成为了无产阶层竞相推崇的造梦偶像。基督山伯爵的剑法再高,也不能比拟他手里那富可敌国的财富实在,那是人们心理最为瘙痒的一层障碍,人们可以对它抛开高尚的虚伪掩饰,尽情地去享受它所带来的快感。基督山伯爵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新一代冒险家们的图腾,他们开始拒绝罗宾汉式的生活,拒绝那个只会劫富济贫的超级剑侠穷光蛋。
西部片中的牛仔往往只会破坏法规等诸多制度,却对个人气节执着不已,很迂腐地坚持着。明眼人都能清楚,这仍然是骑士风度最为关键的一层遮羞布,无论是《火车大劫案》中的比利·安德森,还是《红河》(Red River)中的约翰·韦恩,他们都不能破坏掉这最为微妙的一层规矩。他们可以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可以滥杀无辜抢夺财产,但是惟独不能背叛决斗的规矩,两人要在面对面的条件下显示公平,再参照古老的宫廷规矩同时拔出家伙一决生死。
他们独往独来从不会轻易结党形成势力,他们不会攻击没有武器的人,而只是将最恶毒的办法留给政府的地方银行和邮局。当然,也不会轻易放过荒原上经过的贵族马车,那里总是少不了美丽的小姐和成箱子的珠宝黄金。可以说牛仔们的身上更多包裹着人们对唐吉柯德式理想者的一种补偿化的造梦,他们的武器不该只是对准风车做无用功,而是要有所作为。虽然这个作为开始背叛法律,有违天理,但是这无外乎是一群新的骑士理想者最为实际的一种求生手段。可以说,好莱坞电影中的牛仔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英雄,而是一群实实在在的流氓、彻头彻尾的匪徒、不记生死的好汉、理想化的无产阶级平民骑士。
二、 发展
文学是“看不见听不见的”,电影电视是“看得见听得见”的,正当影迷们还在陶醉于《火车大劫案》那令人目瞪口呆的十分钟时,美国电影工业的第一批西部电影工作者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他们的新作了。他们把平民骑士理想变成了活生生的黑白影像,他们把无政府主义的肆虐形态裸露在百姓们的身边,缔造的主题当然还是那荒蛮的西部,活跃的主角当然还是那些杀人越货的所谓好汉。
与其说好莱坞的制片人们在疯狂追赶一个潮流,还不如说是当时的观众越发对西部好汉产生一种祖鲁式的顶礼膜拜。相对于其他类型电影来说,西部片的结构是极为简单的,简单得乏善可陈,让人回味起来都会感到一丝苍白。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西部片的持续制作与发行,人们对电影的简单理解,以及对一瞬间精彩的心理满足宽容了一切工业化所犯下的错误,人们对原始野性的返璞归真,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忤逆开始成就了西部电影的发展,更成就了一群同样具有牛仔般冒险精神的电影先驱。
《火车大劫案》之后的十几二十年里,比尔·考迪、维亚特·厄普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开始慢慢崛起,他们开始利用自身的才华创造自己理想中的西部英雄,虽然成败各异,但是其成就却开始成为后来者们不断学习效仿的惯用经验。维亚特·厄普曾一度为西部片大师约翰·福特担任创作顾问,这一段经历让最早期的西部片大师们有了凑在一起谈侃经验的机会。在百年西部电影历史中,他们或许算不上是什么革命者,但是没有人会否认,他们的经验交流为无数从事西部片创作的后进们,提供了最为丰厚的思想源泉。
生就于1923年的《大篷车》(The Covered Wagon)无疑也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导演詹姆斯·克鲁茨第一次把真实而壮丽的西部风光搬上银幕,开始脱离影棚时代的双重叠幕影像。另外的一位先行者西西比·波德米尔亲手打造的《消失的美国》、《消失的马车》,在这一时期都非常有代表意义,这样的西部电影有着时代的开拓性与实验性,它们的成功与失落都是伟大的,尤其是在这么一个承前启后的微妙年代。
这样推算而来,诞生于1924年的《铁骑》(The Iron Horse)无疑是幸运了许多,这是西部片大师约翰·福特第一部西部影片,他找到了维亚特·厄普作自己的顾问,他在先行者的成败经验中寻找到了一个便捷的道路,并让大师作为自己的辅佐。他的精明最终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部片宣告诞生,并成为了他自己步向电影殿堂所丢出的第一块敲门砖。
《铁骑》具备了鲜明的美国历史特色,那就是以一种掠夺者的肆虐姿态去戏弄那些为了保护家园而挺身战斗的印地安人。与此同期的西部电影几乎都是一个样子,强盗的优越感开始跃然成为银幕的主角,他们开始冒天下之大不讳自封好汉之名,在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完成屠杀之后,再把标榜为现代文明标志的铁路拓展到未曾被开垦的西部荒原。随即诞生于1929年前的诸如《英豪本色》(The Virginian) 、《原野神驹》(Wagon Master)、《陆路跃进》、《亚历桑那旧事》等代表作品皆莫不如此,西部好汉们的身份已然从一个单纯的无政府主义匪徒,转化为了具备执法职能的拓垦先行官,也可以称之为拥有合法执照的刽子手。这个时期的西部电影已经远离了平民理想主义的初衷,开始成为少数产业家以及农场主们自娱自乐的视觉游戏。一时间违法抢劫火车的跨骑好汉们居然转换了身份,他们不再是旧时的理想偶像,已经沦为一个时代的丑陋污点。
时光回溯到三十年代,这是美国西部片飞速发展与扩张的黄金年代。众多以美国移民拓荒者,以及非法“淘金客”为蓝本的故事开始成为此时期西部电影的主流,科罗拉多大峡谷、亚力桑那荒原以及俄克拉荷马未开垦土地,都成为了电影捕捉的焦点。仍旧是历史的疮疤,它让简单而好斗的美国造梦者经历了一个根本没有法度管束的自由年代,历史渊源在于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联邦政府为了争取群众支持它反对南部奴隶主的战争,于1862年颁布了满足人民土地渴望的“宅地法”。该法案规定,如果没有参加过反联邦叛乱、年满21岁身为户主的美国公民,或申请入籍而没有持枪反抗过合众国的人,只要交纳10美元登记费,就可以申请1/4平方英里尚未分配给私人的公有土地,耕种5年以后,这块土地就免费成为其私有财产。一时,大批的美国人为了拥有自己的土地而涌向西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美国西部土地掠夺大战。
大导演维斯莱·勒格里士在1931年问世的《壮志千秋》(Cimarron)中还原了这一段荒诞的历史,有人称其为西部史诗,或许还是缅怀那个乱纷纷的年代,尊崇于那个被西部外衣包裹着的无政治地带的处女开发吧。1888年俄克拉荷马开放土地,成千上万的人到草原抢夺土地,数不清的马、篷车浩浩荡荡地在大地奔驰,杨西带着妻子莎布拉来到西部草原定居,和一群移民一起艰苦开垦土地。与牧场主的纠纷和斗殴是影片的重头彩,但是最为大书特书的还是杨西见义勇为、劫富济贫的个人行为,他极力维护印第安人的权益,算是个牛仔气质十足的理想化领袖,但是他的身上往往寄托着人们太多的政治渴望,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精神理想而已。
影片对民族共和的歌颂,使得其跳出西部片狭窄的思维路线,成就了一番不太正宗的创作革命。它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艺术指导等三项奥斯卡奖,是美国西部电影最为早期的一座功德碑。虽然说这个功德尚不能改变美国国民对自身价值的褒扬,以及对印第安民族的敌意,但是它毕竟还是积极的创作,尤其是在那个极左思潮横行的伪政治年代。
余外产生于同期的《大追踪》(The Big Tyial)T以及《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都是非常具备时代特色的经典作品,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就是时代痕迹特别浓重,显得特别规矩,也都是由早年著名畅销小说改编而来。
三、
三十年代西部电影是以极度膨胀的姿态充斥于好莱坞影坛的,题材形式不胜枚举,而且多数都在跟风拍摄、粗制滥造,并没有很鲜明的个性与特点。严重的经济危机影响了美国人民的生活,负资产与高失业率成为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好莱坞电影工业不可避讳地受到了冲击,然而,西部片却是个很显著的例外。
就在全美国工业在逐渐步入大萧条时期的前后这几年间,西部片的拍摄反而是以一种疯狂的制作效率,悄然横行在美国影坛。好汉们横枪立马,扬鞭驰骋于大漠的影像开始被人们崇拜而竞相追捧,那或许是等同于人性于彷徨时分,所暗地生就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呼唤着世人冒险的天性与气质,呼唤着人们以一种暴动式的肆虐度过难关,成为自己生活的真正主宰。自从1931年《壮志千秋》(Cimarron)为美国西部电影打开一步登天的大门之后,在短短的十年当中,几百部打着西部旗号的作品招摇着雄霸在好莱坞的二级院线。除了继续罗列一份有名有录的名单之外,我想这些挂着羊头卖得也不一定是狗肉的玩意儿,是很容易被人们所就此遗忘掉的。没有变化,缺乏新意,是这一时期西部片的致命弱点,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它们居然也要比那些主流院线的大制作成功得多,至少在票房收入上,就已是不争的事实。
约翰·韦恩的到来,算是西部片家族在那个年头少有的幸事之一。他是继当年比利·安德森之后再度被推崇的英雄式人物,有了他的加盟,必然会为那些散落在二流院线中的土产西部片,带来一流的商业回报,他值得所有美国西部电影迷们喜爱,更值得人们在最为艰辛的年份给予其精神意义上的信赖。
1939年,西部电影这个几乎快要驶向穷途末路的老马车,终于焕发了一丝由偶像所缔造的生气。这期间先是亨利·金的《荡寇志》(Jesse James)为三十年代末期的西部电影带来创作观念上的转机,而随即由约翰·福特执导的《关山飞渡》(Stagecoach)也顺风顺水地功成名就,其轰动的热力已足以令年富力盛的约翰·韦恩声名雀起、登堂入室。
拿《荡寇志》(Jesse James)与其相比较,如果挑剔点来讲,影片《关山飞渡》(Stagecoach)则更具备了相应的代表性与完整性。它的故事拥有着自身的文学渊源,居然套弄了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名作《羊脂球》。故事的背景从大革命时期的欧洲,辗转腾挪到了美国西部的蛮荒郊野之外。那一辆同样盛载着妓女、银行家和逃犯的驿车单调地驰骋在通往南加利福尼亚的路途上,一路上经受印第安人的袭击、见识小镇上牛仔们的决斗,客观而深沉的个人臆想与沿途破败荒凉的美国西部相应相合,一股子淡淡的悲凉让这个扣人心弦的冒险之旅变得如此狼狈不堪。
约翰·韦恩饰演了那个逃犯,影片之所以成为西部片的划时代经典之作,居然完全不是因为它自身对印地安民族的一番妖魔化,而是它那深邃而无法抑制的旧有文艺韵味。可以说约翰·韦恩的崛起,完全不是他将自身的硬汉本色涂抹得太过浓重,而是得益于他深沉老练的个性。在所谓正义与美人之间,他终于将粗旷的牛仔演绎为挣扎在穷途末路与责任感之间的无产阶级平民骑士,他完整地塑造了一个英雄,一个有气、有节、有礼、有风度的粗线条好汉。
四、
1940年之前的西部电影,虽然对美国拓荒历史颇多涉猎,但是质地却是极为单纯的,主题往往也都不是很鲜明。虽然说偶尔也有精练的手笔,但是大多也得依靠改编文学名著才能换来一份好梗概,但是作用却也极为有限。例如说人物个性的单一,缺少层次变化,缺乏心理积淀的毛病成为了流行弊病,为了疯狂塑造银幕英雄形象,西部片几乎已经沦为了大牌牛仔们的执枪特写写真,令人不得不感到几分厌倦。
直到40年代中期,这样的创作枯竭现象才得以得到缓解,1946年,以《太阳浴血记》(Duel In The Sun)、《不法之徒》(The Outlaw)等新兴西部片为代表的电影作品开始成为真正的主流,电影人开始将“性”的元素赤裸裸地搬到了银幕上,开始让西部片以一种新现实主义的姿态成为好莱坞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代表性流行符号。这一时期的西部片开始真正地缔造自身的流行特点,快枪、快马、强权、平民、野店、警长、妓女、贵妇、淘金客、复仇者、逃犯、流浪汉、嬉皮士等成功的形象也开始成为其它类型片竞相效仿的渊源。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西部片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程序与规模,已经成为了好莱坞电影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串串色味俱佳的午餐肉了。
这个时期的西部片多数都很变异,例如第一次将性爱与西部题材挂钩的《不法之徒》(The Outlaw),以及有着浓厚黑帮色彩的西部片《绝初逢生》(Pursued),都是将现代社会最为流行的话题带入到好莱坞的大银幕。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使得西部片没有过早地丢失时代特色,落后在流行文化的边缘。随即新的创作概念已经开始涉猎各种题材,比如说赌博与彩票等社会现象,也成为了西部片竞相吸纳的好段子。 相对于喜欢追求新鲜刺激的霍华德·休斯(《不法之徒》1946)与威廉·维尔曼(《龙城风云》1943)来讲,这时期的约翰·福特依旧是古典主义英雄观最为忠实的捍卫者,他在《侠骨柔情》(My Dar-ling Clementine)当中继续挥洒着当年维亚特·厄普的一脉豪情,并无限度地将这种最为古典英雄主义情结浪漫化、史诗化。他最终仍获得了人们多数的赞誉与好评,虽然他的电影早已经没有什么新鲜元素与创造性突破,但是质地却永远是细腻而丰满的。以战后美国人沉浸于英雄主义精神反思的角度来看,这种旧有的品味,仍旧是当仁不让的主流。
《红河》(Red River)诞生于1948年,这是美国西部片百年历史的不朽丰碑,更是大导演霍华德·霍克斯为四十年代西部电影乐章划上的最为辉煌的一笔休止符。故事的脉络很简单,约翰·韦恩仍旧是绝对意义上的主角,但是影片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鏖战,或是发生惊世骇俗的生死恋,它只是讲述了一个关于背叛与复合、爱情与友情之间的小涟漓。韦恩是一个顽固倔强的老农场主,而年轻牛仔加斯却因为一点小风波就与他决斗,随后又偷偷赶走他的那1000头黄牛。我的上帝,要知道,那是一千头活生生的牛,它们浩浩荡荡地行走在荒原上,或在牛仔的趋赶下向前缓行,或被野兽惊吓后怒吼狂奔……要知道这种大场面只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才被凯文·科斯特纳在《与狼共舞》(Dance With Wives )中还原,最古老也最原始的那一幕是让人们牢记时代更迭,回顾沧桑巨变的不二法宝。可以说《红河》(Red River)的伟大,单纯地在于它的小概念结构下的大场面追逐,这是世界电影史上最为伟大的尝试之一,它为西部片家族带来了一份革命意义上的光荣。
五、
直到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好莱坞的西部电影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链,一大批有着市场影响的演员和导演都已经被大众认可,可以说,西部片已经打造了自身的黄金招牌,不光是吸引着无数青年才俊加盟进这个团队,更利用自身的流行特性塑造一座座真神一般的银幕偶像。约翰·韦恩当然是当仁不让的王者,然而诸如像加利·古柏这样的冷面英雄也开始慢慢地大行其道。
加利·古柏的成名源自于一部伟大的西部片《正午》(High Noon),这部诞生于1952年的电影,应该算是西部片创作从幼稚取材而走向成熟结构的里程碑。故事中,加利·古柏饰演的小镇警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几个曾被他亲手送到法庭的牛仔要赶回来报仇,战贴已下,时间就约在正午时分的十二点正。然而警长已经选择离任,他即将陪着妻子乘火车返回故乡,但是男人的责任心以及对小镇的担心促使他留了下来,留下来见识到了身边人冷漠的心态以及无情的推卸。他最终选择一个人对付进犯的匪徒,一个人对付四只黑洞洞的枪口……
影片获得了奥斯卡大奖,加利·古柏成为了继约翰·韦恩之后再度被评论界追捧的赢家,韦恩亲自将小金人交于古柏的手上,虽然他并不情愿,韦恩曾一度很反感影片《正午》(High Noon)的那个黑色的结尾--风波平息之后,古柏警长居然将陪伴他多年象征荣誉与责任的警徽丢到了脚下。韦恩说这是对国家与责任的亵渎,但是人们很清楚,这样的行径才是一个看破世态炎凉的老牛仔所应该做的,也是他在获得新生之后仅有的选择。
有伟大的,就有失落的!每当我们翻看奥斯卡最佳名录而回溯美国电影历史的时候,或许都不会想到它--一部质地优异,堪与《正午》(High Noon)同等分量的西部电影《搜索者》(The Searchers )。影片拍摄于1956年,是西部片之王约翰·韦恩的颠峰之作,影片依然维系着韦恩惯有的西部末世豪杰路线,陈旧而沧桑,与印地安人的仇恨与纠葛仍旧是故事的主题,不同的是,它通过主人公潜在的罪恶思想砸碎了旧有的英雄观,而是让仇恨在死亡决斗之后更加沉重。韦恩在结尾时的告白很简单,只是简单的一句:“我们回家吧……”正如美国人以掠夺者自居之后再度负疚反思历史一样,只有这么轻描淡写而已,没有强调是谁造成的过错。
影片居然没有获得一项奥斯卡提名,这让很多行家都感到困惑与不解,或许仅只是影片的主题过于晦涩暧昧的原因,以至于奥斯卡评委们没有猜透韦恩到底是在表现些什么。在他们的眼里,西部电影应该是壁垒分明的东西,需要一个光明磊落的主题,要么复仇、要么悔过,根本就不需要玩弄如此深沉而令人费解的洒脱。
五十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无数具备相当水准的西部片开始步入到好莱坞经典电影的殿堂。不仅有《正午》(High Noon)、《搜索者》(The Searchers )这样伟大的电影开创时代潮流,而且以《原野奇侠》(Shane)、《枪手》(The Gunfighter)、《印地安纳要塞》(Fort Apache)、《格兰特河》(Rio grande)、《她系了一条黄丝带》(she Wore a Yellow Ribbon)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西部片,开始被人们无数次地谈论、揣摩。对于西部片影迷来说,这是一个多么振奋人心的激情年代,它们不仅让战后的美国人民重新拣回了丢失掉了的奋斗精神,更让全世界人民都记住了这些来自于美国西部荒原的游侠、流氓、淘金客。 继二十年来约翰·韦恩与约翰·福特这样的黄金搭档独霸好莱坞西部片市场之后,五十年代开始涌现更多的影坛新生力量。詹姆斯·斯图尔特与大导演安东尼·米恩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组合同样也受到人们的追捧,无论是市场成绩还是评论口碑都让人艳羡不已,可以说,他们才是五十年代西部片具有相对统治力的代表人物。
另外坚毅而冷静的简·方达,犹如石雕一般的兰道夫·斯科特,外冷内热的柯克·道格拉斯,委屈得象受气包一样的乔尔·迈克利,不留情面的里查德·维德马克,都是人们在那个年代挥之不去的记忆,在许多怀旧影集当中,他们总是占据着最为耀眼的位置,展示自身特有的男人风骨。可以说,他们是最有男人味的一代人,他们的思想完全可以脱离肢体语言通过雕塑一般的轮廓来表达,他们主演的西部电影不一定是最酷的电影,但是他们却绝对当仁不让地可以被称为是最酷的一代人。
六、
现代的电影评论者总在很不要脸地重复着两个论调,第一就是美国西部片,是否从早期日本剑侠电影中掠取了太多营养;第二就是在另一个半球搞西部电影的他们,是否真的疯狂地崇拜着日本电影教父黑泽明。根据无一例外地指向了拍摄于1960年的《豪勇七蛟龙》(The Magnificent Seven Ride!) ,因为影片的题材与梗概的确是翻版了黑泽明的剑侠电影《七武士》,这样的做法遭到了鼓励原创作品的评论界异口同声的歧视,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惩这种口舌长短的人仍旧占据大多数。
要知道,日本民族电影工业发展较晚,1950年之前,相对于同时代的中国上海电影,它也只能算是不入流的小弟。后期日本电影真正形成工业的时代,也是从五十年代末,全日本开始走出二战阴影摆脱经济灾荒的时期算起。这一时期他们多半都是在世界电影这个大家庭里疯狂吸取营养,而没有相对成熟的电影经验可言。
在被后人重新整理考证后的人物传记中我们得知,黑泽明拍摄剑侠、武士电影其实并不偶然,他一半是在传统武士小说中结构自身的历史见识,而更多时候还会在大量美国早期西部电影中寻找拍摄经验。他认为,牛仔们的决斗方式,以及西部片为他们提供的氛围,完全合乎日本剑侠们的行为以及人们的直观接受能力,所以他将这些用枪说话的牛仔们转换为日本传统故事中的浪人武士,同样的冷峻、同样的沉默寡言、同样两边对立公平决斗,同样一块掏出家伙在电光火石之间完成生死游戏。
《七武士》更像是一个被改编了的野本子《群侠列传》,其中似乎还深深埋藏着《火车大劫案》(The Grant Train Robbery )时初期西部电影的影子。要知道早期银幕上的牛仔并不是独往独来、单打独斗,他们更多是像《火车大劫案》中四个人一伙作一些见不得人的买卖。火车上四个人各自对付执法者的无声画面成为了黑则明最早的电影启蒙,而与他后来打造《七武士》时不同的概念是,杀人越货的匪徒一转眼转变为了替天行道的执法者,他们不再为个人私利做生死冒险,而是为了素不相识的无辜百姓免费讨回公道。可以说,黑则明的这一招是刻意而为的,他对《火车大劫案》(The Grant Train Robbery )的颠覆欲的确很少有人联想得到,而他对美国西部电影的崇拜,似乎也只有在接受几家美国主流电影评论媒介采访时才被略微提到过。毕竟大师的潜意识里还是要保留自身民族主义的那点劣根性,成名以前当然要以学徒的方法做事,成名以后当然要以大师的口吻宣功立德了。
改编自《七武士》的《豪勇七蛟龙》(The Maginicent Seven )获得了相对意义上的成功,七个好汉联手打天下的创造性模式改变了多年来人们对西部片的简单看法。个人英雄主义的风气开始刹车,鼓励团结协作、歌颂友情的创作风气开始慢慢抬头。原本以为生于1960年的这部电影,会利用自身的成功特点为好莱坞西部片再创一个黄金时代,但是又有谁会想到,当我们厌倦个人化英雄独闯天下、单枪匹马改造旧世界的时候,西部电影事实上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事实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部电影工业,已经走向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对于西部片最为沉重的打击,就莫过于是偶像的离开,约翰·韦恩的老迈与加利·古柏的死,让习惯让偶像们迸放魅力的西部电影变得如此的苍白。在这十年当中几乎没有谁可以再造西部片的辉煌了,虽然说偶尔也会涌现出《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与《大地惊雷》(True Grit)这样的精品,但是人们对它的热情似乎早已丧失殆尽,人们已经开始厌倦一成不变的历史题材成人童话麻痹自己,而是需要一些更为深邃的东西来丰富自己的人生观。
60年代中期开始,意大利电影工作者曾经一度试图复兴西部片的辉煌,但是成绩也不是很可观。1964年意大利人赛尔乔·莱昂内开始了意大利式西部片的尝试(外景地在西班牙)。在他的西部片中人物已不再善恶分明,而是沾染了“黑色电影”的脾性,反英雄,非主流,反乌托邦,颠覆传统。每个人都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正面角色。他的金钱三部曲获得了成功,把“通心粉西部片”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一起带给美国观众。
赛尔乔·莱昂内一辈子致力于拍摄美国英雄故事,一个意大利人的幻想中的美国西部传奇故事。在拍摄《好的、坏的和丑的》(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The 1966)、《从前在西部》(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1968)之前,赛乔奥还不会说英语,他根本不清楚美国是个什么鸟样,他只关心自己心目中的美国故事好不好玩。从《荒野大镖客》到《黄金三镖客》再到《意大利西部往事》,来昂内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意大利式西部传奇。但是他不可能拯救得了西部片的彻底没落,在满足完欧洲观众的新鲜感之后,他自己也不得不刹车转业,结束掉了自己的美国西部片之旅。要知道,这个老鬼一直到了1984年时,才第一次见识到真实的美国。
“当你写一个关于意大利的故事的时候,你只能写意大利。可是在美国,即使是一个最小的小镇,你可以写关于全世界的故事。为什么?因为美国是所有社会群体的聚集地。你可以在美国找到全世界。”
--赛尔乔·莱昂内
七、
从七十年代开始,好莱坞西部电影就已经在世面上全线溃退了。1976年,老迈的约翰·韦恩在《神枪手》(The Shootist)中做了自己最后的告别演出,影片很快在好莱坞新一伦的造梦狂潮中淹没,但是约翰·韦恩却传奇依旧,他成为了人们对美国西部最为永恒的记忆,任凭时代更迭也难以让人淡忘。
这一时期似乎只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仍旧活跃,他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积累经验与人气,并且自己做导演拍摄电影,坚持磨历自己的风格,一直将自己的西部之梦从1976年的《西部执法者》(The Ontlaw Josey Wales)坚持到了1985年的《苍白骑士》(Pale Rider)。对于那些逝去的前辈们而言,他的这些小小成绩几乎是微不足道,但是好在他还在坚持梦想,在现代社会声色犬马、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里,他像是一个来自于古代传经卫道士,虽然磕绊不断,但是他仍旧选择坚持。
我不想提起好莱坞的八十年代,除了仍旧选择几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西部片之外,我几乎已经想不起还有什么可值得我们缅怀一下。或许也应该提一下瓦尔特·希尔的《骑士》(The Long Riders),虽然它的粗糙已经让很多人不堪忍受,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喜欢沉浸在西部梦幻里的俗人来讲,已经能够有一点小小满足了。
直到1990年,沉寂了十几年的西部片领域终于有了一点涟漓,一个叫做凯文·科斯特纳的中年男人横空出世,他趁着自己还没有完全耗尽青春资本之前选择了西部片,让这个几乎是已经告别历史舞台的类型片奇迹般的焕发了生机。这就是至今仍旧被我们念叨的《与狼共舞》(Dance With Wives),一部古典得发黄、纯熟得发烫的经典西部作品,南北内战、印地安人、边陲塞外、野牛奔流、简易哨所,一切都还是那么的似曾相识,那么样恢弘古朴。它不仅仅只是为自身带来六项奥斯卡大奖,而且呼唤起了所有曾喜爱着西部风骨的人们对新时代美国西部电影的信心与憧憬。
独自选择涉足塞外的巴里中尉,与执意走进西部片领域的凯文·科斯特纳是那么的相似,他们都是在感知一种精神上的孤独之后,才把自己放逐在一个不被人惊扰蒙蔽的荒原。相对于从前的西部片而言,凯文几乎是选择了一种最为古老而冒险的概念,他将《壮志千秋》、《亚历桑那旧事》中的战乱历史追溯移植过来,以战争创痕开篇,再以《铁骑》、《关山飞渡》当中与原住土著居民的民族矛盾作为基础,再以战争结束。人与人之间从仇视到交融、从不解到任知,几乎就像是推开一扇门那么简单,那种疏离的感觉很微妙,他不仅让故事的脉络变得很简洁委婉,而且更使其延伸出千枝百节的潜在喻义,用暧昧的手段去阐述很明了的主题,凯文独特的创造力,使影片催生了惊人的魅力。
《与狼共舞》的影像是陈旧的,那种旧有的品味,几乎是对逝去的那个时代举行最后的一场祭祀。看到了印地安人在峡谷中猎取奔牛的宏伟场面,我们登时会想到那1948年的《红河》,作为一种祭祀,最好的方式无非就是还原它的经典画面,凯文这么做了,他让野牛的狂奔引领着自己的摄影机由远到近、由近到远,影史上那最为伟大的一幕终于被还原,而凯文作为新一代的西部英雄,终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掌握到了一个平衡的支点。
《与狼共舞》的成功让人感到有点突然,在好莱坞已经开始向高科技武装彻底投降的九十年代,他的崛起,则更象是受到了阔老施舍而暴福的孤儿。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受宠过,他没有为西部片带来最终的奇迹,而是象一朵骤然开放的昙花一样,转瞬即不见。
两年之后,凯文科斯特纳没有继续坚持自己的西部梦幻,而是转业玩科技,结果大家是清楚的,一败涂地而已,这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选择放弃这个孤独的巴里中尉了,只能够继续支持那已经日渐苍老的科林特·伊斯特伍德。诞生于1992年的《不可饶恕》(Unforgiven)是他艰难的一次喘息,在嘈杂纷扰的现代社会,我们似乎只能做如此低能的判断,科林特·伊斯特伍德要捍卫自己的尊严,正如影片中那个为了争回面子重树声名的那个老牛仔一样,他需要一个能焕发自己光辉的空间与角落,虽然你可能只是用快枪单独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敌人,也或是只是简单对付自己的虚荣心而已,但是他必须要这么做下去,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来自西部、曾经拥有荣耀的牛仔。
辉煌的《与狼共舞》与《不可饶恕》,最终还是沉寂在了九十年代电影之林,虽然它们都敲开了奥斯卡的大门,虽然它们都获得了相对可观的商业成绩,但是它们却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立足基点。
也可以更确切而且是更为沉痛地说,是在这个好莱坞利用高科技武装制造未来式梦幻的尖端时代,它们--那群苍老而没落的牛仔们--那些过气而陈旧的西部电影……它们根本就已是无法安身立命,苟延残喘,直至死无葬身之地。
八、
2003年有了《失踪》,导演朗·霍华德很想和在西部片领域塑造过辉煌的前辈们一样,利用改编著名文学作品这个契机为自己树碑立传。它的故事很简洁,没有什么特别出奇之初,虽然导演朗·霍华德还指望着它能给自己打开奥斯卡这个沉重的大门,但是影片最终的平淡反响,还是让他带着满身遗憾落寞地走开了。
2003年有了《天地无限》,曾经以西部片《与狼共舞》在世界电影圈中引起轰动的凯文·科斯特纳,再次在影片中上演与狼共舞的好戏,只不过对手不是一匹真狼,而是一个狼心狗肺的美国西部小镇的行政长官。这部由试金石公司投资4500万美元拍摄的影片最终也落寞收场,它没有打动奥斯卡的评委也没能征服观众,一切的结果就象是凯文·科斯特纳那全新而恶毒的造型,失败又失败。
时代的更迭,历史的变迁,人们的眼光随着光怪陆离的数码影像而变得异常挑剔而漠然。西部片少了,也或是说西部片已经濒临绝种了,要知道200某年之后,或许世界电影百科词典中就不会再有西部电影这个名词了,所以我们提前溅点口水,以示怀念。


 21世纪中国前沿影视论坛 → 电影专业区 → 影片分析 → 百年西部片——西部片之“初”
21世纪中国前沿影视论坛 → 电影专业区 → 影片分析 → 百年西部片——西部片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