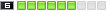谈什么北大精神? 转帖
谈什么北大精神?
读者:Thomas
2006年8月18日 星期五
FT中文网编辑:
您好!读了许知远的《走向封闭的北大精神》,谈点儿感想。
从上世纪下半页开始,兼容并包就没有了,独立与自由也不见了,谈什么北大精神?
虽不是文革的始作俑者,也是点第一把火的小丑,谈什么北大精神?
某某年以后,更是噤若寒蝉,无视民生艰难,淡漠百姓疾苦,抛弃民族文化,模糊前进方向。于象牙塔里,拾点牙慧;故纸堆中,卖些风骚,谈什么北大精神?
现在只有媚俗、流俗、拜金、弄权,不配再叫北大,更不配提北大精神!
所以,你的文章题目就错了。
一个没有文化的校长已经足以让北大蒙羞了(要是北大还知道羞耻二字的话),一个没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北大更让中国人蒙羞。
别谈什么北大了。一个既不能领袖群伦,荷担民族文化精神发展的重任,又不能特立独行,发扬民主自由精神的学校,和我读的三流大学有什么区别?稍强一点的地方就是北大或可被称为留美预备班罢了。
再看看北大的学生,不是书呆子就是投机政客,可以因需要高喊反美口号再嫁给美国人,也可以销尖脑袋钻进中央部委,混个脑满肠肥的处长、局长,狗苟蝇营,哪里还有拯万民于水火的壮志豪情?何况那点青年的冲动,在大学一年级就被教育光了吧?
有什么样的大学,就有什么样的学生 (抱歉,不是想攻击许知远老弟,许先生必是北大人里的异类,少有的清醒者);有什么样的学生,就有什么样的大学。
不熟悉北大的老师,就不谈了──北大还有可被称为师尊的巨匠么?
可叹!可惜!可悲!可泣!
但不可歌,因为可歌者都已成为极其遥远的过去。
读者:Thomas
------------------------------------------------------------
走向封闭的北大精神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6年8月17日 星期四
1998年5月4日的北大,像是一场盛大的、期盼已久的游园会。我是一名三年级学生,住在28 楼的105室,刚刚七点钟,就被吵闹声惊醒。
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新闻事件,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这所大学和她的国家命运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使在世界历史上都少有例证。
我记得那天的奇特感受,那种混合着骄傲和不安嘲讽的心理。几个月前,北大南门矗立了设计简陋的倒计时牌,告诉你还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就是她一百年的庆祝,它是天安门广场上迎接香港回归倒计时排拙劣的仿制品。报纸上充斥了这样的消息,欧美校友包专机从海外归来,南方校友在深圳包了专列返回母校,中国铁路史上从未有专为一所大学开办的专列……
校园里拥挤了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校友,从西南联大时期的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到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但他们似乎不是这一事件的主角。庆祝的典礼不是北大校园里进行,而是人民大会堂。那些从各系挑选的学生代表,在那里迎接这场庆祝的高潮—— 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演讲。
和政治含义同样显著的,还有它的商业味道。学校里盒饭和各种纪念品的兜售,使校园像是一个大型的市场,出版商与电视台不断的推出与北大相关的产品,但是当我试图寻找一本完整的北大历史时,却毫无收获。我们还被不断告知,因为这场庆典,学校又收到了多少捐款,它将用于修建多少层的高楼。
这一切和那个令一代代人念念不忘的北大有什么关系。每一个入学的青年,都曾经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原则带来的群星灿烂的年代憧憬不已,每个北大人都为鲁迅的名言激动:“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但是念来念去,我们所有的感慨与追忆都发生在 1917年——1929年那个短暂的时代。辉煌的西南联大时代的似乎更是清华大学的产物,而在混乱的文革年代,北大的表现或许更令人汗颜。在一个被普遍视作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黄金时代的八十年代,北大的性格没有那么鲜明,那个年代公认的知识领袖来自于其他大学与机构。以至于在风靡一时《北大往事》时,我们被打动的是年轻人的嘻笑怒骂式的琐碎追忆,而不是某种更崇高和富有创建性的品格。甚至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燕园,也是斯徒雷登的遗产。
九十年代的北大时光是暗淡的。政治气氛的压力无处不在,北大在突然到来的全国性商业浪潮前慌乱不堪。拆了南墙,不是为了以大学独特的精神去影响社会,而是变成了社会风尚的俘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所学校的真正骄傲似乎变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门外的北大资源楼里一家接一家的小公司里,都以北大为旗帜,那个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缔造的光辉名字,成为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优秀的年轻人仍蜂拥而来,因为中国的大学比国营企业更为顽固和拒绝改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在90 年代的最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学生扩招为大学带来大跃进式的风潮,人人都在谈论世界一流大学,却忘记了大学的基本理念。即使在战时、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仍在相信“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
2000年毕业之后,我已很少回到校园。社会上关于北大的消息一直没有中断过,我听到了卖猪肉、卖糖葫芦的北大学生,听到了那场轰动一时、却似乎无疾而终的改革,最近的消息是北大拒绝让那些小学生前来参观,她准备关闭校门,她还和一位著名数学家发生了争吵、却又提不出值得信赖的反驳,她不满于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打乱了她自己的招生计划……像是一个任性、傲慢、却又缺乏竞争能力的孩子,神形又是如此的老态龙钟。
1992年拆除的南墙重又建好,校园的东北角矗立着太平洋电脑城,那里面闹哄哄景象令人烦躁。在和隔壁的清华大学一起叫嚷着要成为斯坦福大学,将中关村塑造成硅谷多年之后,此地仍是小商小贩的天下。
如果没有伟大的大学,我们会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吗?如果一个国家最著名的大学,都缺乏反省精神,缺乏对于自己使命的明确认识,这个国家能寻找到自己的方向感吗?
我们尊敬的北大,是那个作为思想的实验场,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作为新知识的探索者,作为高级的精神生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的北大。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北大精神早已走向封闭,很多年以来,我们依靠的不断重复回忆,来欺骗自己我们与这股伟大传统依然相联。


 21世纪中国前沿影视论坛 → 灵感泉——电影之源 → 社会热点|新鲜生活 → 谈什么北大精神? 转帖
21世纪中国前沿影视论坛 → 灵感泉——电影之源 → 社会热点|新鲜生活 → 谈什么北大精神? 转帖